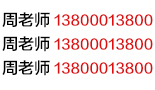热点新闻
联系方式
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
培训一部:0539—8025001
培训二部:0539—8025001
培训三部:0539—8025001
培训四部:0539—8025001
后 勤 部:0539—8025001
网络宣传:0539—8025001
邮箱: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沂市文化中心14楼
红色传人
周恩来果断纠“左”
时间:2017-12-01 14:49 来源: 作者: 点击:
次
中央苏区的肃反,起源于1930年2月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这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久便和反“AB团”纠缠在一起。
何谓“AB团”?“AB”团的“AB”是英文Anti一 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1926年9月,蒋介石通过陈立夫派遣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等人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江西考察党务。11月又派洪轨到南昌,开始筹划建立反共秘密组织——“AB团”。蒋介石策划成立“AB团”,目的是反对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1927年1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AB团”通过阴谋手段,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权,但随即遭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击。3月下旬,南昌市工人和民众反对省党部、省政府的声势日增。同年4月2日,中共江西区委发动南昌人民举行大暴动,一举打散“AB团”组织,抓捕其骨干分子程天放、曾华英等30余人,并进行了公审批斗。其人马随即各奔东西,如鸟兽散。此后,“AB团”组织再也没有恢复,散于各地的零星“AB团”分子也渐渐销声匿迹。
由于“AB团”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的,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对此很重视,一再指示江西党组织要反对“AB团”,要积极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而且,当时根据地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确实存在。如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因坏人告密而在安福县境遭到地主武装袭击牺牲;总前委3个优秀警卫员被秘密杀害;在对敌作战时,有人煽动哗变;行军时,有人故意破坏群众纪律;红军经过的地方,出现反动标语等等,也容易被误认为是“AB团”、改组派所为。
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6月至9月间,忙于从汀州向长沙进军和第二次攻打长沙,没有过问肃“AB团”问题,撤围长沙并于10月初攻克吉安后,在过问地方工作时,发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来的“AB团”分子竟占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一。这引起了总前委的震惊,认为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同时将这一错误估计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根据报告认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包括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府乃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都充满了“AB团”。此后,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多次讨论肃“AB团”问题,认为赣西南党内、团内和各级政府内由于充满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缘故,要全部改造。
罗坊会议作出了“诱敌深入”的正确决策,但同时,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作出了进一步抓地主富农和“AB团”的决策,导致抓地主富农和肃“AB团”的错误愈演愈烈。从11月初开始,红一方面军从总政治部到下级连排进行肃反。各军都成立肃反委员会,师、团、营、连、排都成立肃反小组。在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打了四千“AB团”。据萧克回忆,当时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总前委和四军军委都不干涉,结果, “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滥抓滥杀的结果,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富田事变”发生不久,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中央工作脱不开身,不能到职,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项英一上任就遇到处理“富田事变”这个复杂又棘手的问题。他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和证据,全面、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严肃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错误,达到了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稳定人心、避免分裂的目的,从而一度缓解了赣西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项英纠正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的工作仅仅进行了三个月,就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彻底否定了,撤了项英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另派代表团重组苏区中央局。重组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力支持总前委,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严厉批评项英是“脱离阶级立场”,“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这样,反“AB团”的错误再一次恶性发展起来。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局面。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一肃“社会民主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12月18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恩来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他沿途作调查,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到中央苏区之后,立即以主要精力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第一,批评了夸大敌情的错误。苏区之所以一度出现“肃反中心论”,主要原因就是夸大了敌情,导致肃反措施失当。早在1931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就指出:苏区内现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3月28日,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过分地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8月30日发出的、由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强调:“AB团是地主残余与富农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AB团是反革命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反革命派别在苏区便一定是AB团;党的错误路线,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甚至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故(固)可被AB团拿来故意做错来毁坏党的信用,但不是每一个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做错了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都是AB团。”因此,“绝对不能在解释和处理这些斗争(时)都笼统作AB团看待”。
第二,采取组织措施,让苏区肃反扩大化紧急刹车。在赣西南,处分了滥用肃反大权、民愤极大的李韶九。李韶九在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曾被开除党籍,可惜后来没有执行。富田事变后,李韶九不仅是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主任,还兼任了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权力更大了。他倚仗总前委的支持,恣意妄为,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冤杀了大量无辜。因此,中央局决定撤销李韶九的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在闽西,周恩来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起草致闽西党的信,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林一株,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不少党员干部成了他肃“社民党”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冤魂。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信以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8人为闽西“社民党”核心人员,分别处以死刑。
第三,制定法律法令,健全司法机关。原来的各级肃反委员会失去监督,权力无边。他们处置犯人完全不讲什么制度程序,助长了滥捕滥杀的恶性发展。针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从法律程序和具体制度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六号训令。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察、逮捕和预审,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之后以原告人资格,向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出公诉,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一切反革命案件审讯(除国家政治保卫局外)和审决(从宣告无罪到宣告死刑)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死刑之权,……中央区及附近的省司法机关,作死刑判决后,被告人在十四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在审讯方法上,为彻底肃清反革命组织,及正确地判决反革命案件,必须坚决废除肉刑”。在1932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中更规定:“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拘捕审问权属于政治保卫局,政府其他机关、共产党部、青年团部及一切革命团体均不得自行拘捕审讯,尤其不得自行处决,……”;“对于惩罚反革命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查的原告地位”。
第四,形成肃反决议,规范苏区肃反工作。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首先提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指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由上海赴中央苏区途中“关于闽西肃反所犯错误”给中央政治局的信。由此可见,周恩来纠正肃反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上升为中央的意志。
《决议案》在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之后,重申了1931年8月30日由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所论述的苏区在肃反认识上的错误,认为“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
《决议案》分析了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认为“党内对AB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他思想的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反相信AB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广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AB团是肃清不了的”。
《决议案》严正指出:“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问相互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回反革命欺骗影响下的群众;相反的,反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决议案》强调,中共苏区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澈底的转变”,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认为“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方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
《决议案》最后要求,“这一决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并将执行的情形于二月(远的省份迟至三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绎讨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肃“社民党”运动逐渐停止。1932年春,周恩来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钱壮飞还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从此以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起了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中央苏区再没有开展过像反“AB团”、肃“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大规模肃反运动,群众中的恐怖情绪逐渐得以消除,苏区各项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这是周恩来在苏区工作中的一大贡献。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影响,以及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人“左”的错误干扰,也由于周恩来本人当时认识上的局限,因此没能从根本上纠正肃反错误。
何谓“AB团”?“AB”团的“AB”是英文Anti一 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1926年9月,蒋介石通过陈立夫派遣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等人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江西考察党务。11月又派洪轨到南昌,开始筹划建立反共秘密组织——“AB团”。蒋介石策划成立“AB团”,目的是反对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1927年1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AB团”通过阴谋手段,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权,但随即遭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击。3月下旬,南昌市工人和民众反对省党部、省政府的声势日增。同年4月2日,中共江西区委发动南昌人民举行大暴动,一举打散“AB团”组织,抓捕其骨干分子程天放、曾华英等30余人,并进行了公审批斗。其人马随即各奔东西,如鸟兽散。此后,“AB团”组织再也没有恢复,散于各地的零星“AB团”分子也渐渐销声匿迹。
由于“AB团”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的,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对此很重视,一再指示江西党组织要反对“AB团”,要积极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而且,当时根据地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确实存在。如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因坏人告密而在安福县境遭到地主武装袭击牺牲;总前委3个优秀警卫员被秘密杀害;在对敌作战时,有人煽动哗变;行军时,有人故意破坏群众纪律;红军经过的地方,出现反动标语等等,也容易被误认为是“AB团”、改组派所为。
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6月至9月间,忙于从汀州向长沙进军和第二次攻打长沙,没有过问肃“AB团”问题,撤围长沙并于10月初攻克吉安后,在过问地方工作时,发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来的“AB团”分子竟占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一。这引起了总前委的震惊,认为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同时将这一错误估计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根据报告认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包括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府乃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都充满了“AB团”。此后,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多次讨论肃“AB团”问题,认为赣西南党内、团内和各级政府内由于充满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缘故,要全部改造。
罗坊会议作出了“诱敌深入”的正确决策,但同时,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作出了进一步抓地主富农和“AB团”的决策,导致抓地主富农和肃“AB团”的错误愈演愈烈。从11月初开始,红一方面军从总政治部到下级连排进行肃反。各军都成立肃反委员会,师、团、营、连、排都成立肃反小组。在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打了四千“AB团”。据萧克回忆,当时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总前委和四军军委都不干涉,结果, “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滥抓滥杀的结果,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富田事变”发生不久,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中央工作脱不开身,不能到职,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项英一上任就遇到处理“富田事变”这个复杂又棘手的问题。他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和证据,全面、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严肃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错误,达到了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稳定人心、避免分裂的目的,从而一度缓解了赣西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项英纠正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的工作仅仅进行了三个月,就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彻底否定了,撤了项英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另派代表团重组苏区中央局。重组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力支持总前委,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严厉批评项英是“脱离阶级立场”,“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这样,反“AB团”的错误再一次恶性发展起来。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局面。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一肃“社会民主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12月18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恩来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他沿途作调查,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到中央苏区之后,立即以主要精力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第一,批评了夸大敌情的错误。苏区之所以一度出现“肃反中心论”,主要原因就是夸大了敌情,导致肃反措施失当。早在1931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就指出:苏区内现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3月28日,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过分地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8月30日发出的、由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强调:“AB团是地主残余与富农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AB团是反革命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反革命派别在苏区便一定是AB团;党的错误路线,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甚至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故(固)可被AB团拿来故意做错来毁坏党的信用,但不是每一个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做错了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都是AB团。”因此,“绝对不能在解释和处理这些斗争(时)都笼统作AB团看待”。
第二,采取组织措施,让苏区肃反扩大化紧急刹车。在赣西南,处分了滥用肃反大权、民愤极大的李韶九。李韶九在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曾被开除党籍,可惜后来没有执行。富田事变后,李韶九不仅是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主任,还兼任了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权力更大了。他倚仗总前委的支持,恣意妄为,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冤杀了大量无辜。因此,中央局决定撤销李韶九的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在闽西,周恩来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起草致闽西党的信,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林一株,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不少党员干部成了他肃“社民党”运动中滥杀无辜的冤魂。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信以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8人为闽西“社民党”核心人员,分别处以死刑。
第三,制定法律法令,健全司法机关。原来的各级肃反委员会失去监督,权力无边。他们处置犯人完全不讲什么制度程序,助长了滥捕滥杀的恶性发展。针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从法律程序和具体制度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六号训令。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察、逮捕和预审,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之后以原告人资格,向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出公诉,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一切反革命案件审讯(除国家政治保卫局外)和审决(从宣告无罪到宣告死刑)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死刑之权,……中央区及附近的省司法机关,作死刑判决后,被告人在十四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在审讯方法上,为彻底肃清反革命组织,及正确地判决反革命案件,必须坚决废除肉刑”。在1932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中更规定:“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拘捕审问权属于政治保卫局,政府其他机关、共产党部、青年团部及一切革命团体均不得自行拘捕审讯,尤其不得自行处决,……”;“对于惩罚反革命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查的原告地位”。
第四,形成肃反决议,规范苏区肃反工作。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首先提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指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由上海赴中央苏区途中“关于闽西肃反所犯错误”给中央政治局的信。由此可见,周恩来纠正肃反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上升为中央的意志。
《决议案》在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之后,重申了1931年8月30日由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所论述的苏区在肃反认识上的错误,认为“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
《决议案》分析了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认为“党内对AB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他思想的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反相信AB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广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AB团是肃清不了的”。
《决议案》严正指出:“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问相互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回反革命欺骗影响下的群众;相反的,反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决议案》强调,中共苏区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澈底的转变”,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认为“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方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
《决议案》最后要求,“这一决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并将执行的情形于二月(远的省份迟至三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绎讨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肃“社民党”运动逐渐停止。1932年春,周恩来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钱壮飞还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从此以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起了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中央苏区再没有开展过像反“AB团”、肃“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大规模肃反运动,群众中的恐怖情绪逐渐得以消除,苏区各项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这是周恩来在苏区工作中的一大贡献。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影响,以及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人“左”的错误干扰,也由于周恩来本人当时认识上的局限,因此没能从根本上纠正肃反错误。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